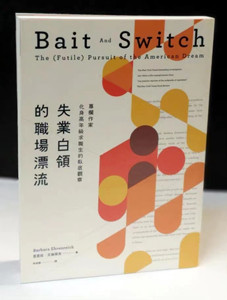當代人面臨的基本社會觀念是:人的社會價值完全取決于他的經濟價值。人的經濟價值,要么體現為投資性收入,要么體現為勞動性收入。但投資性收入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自己有沒有順利在正確的時間上車,不完全是運氣但強烈依賴于運氣。如果拋開那些有投資性收入的幸運兒不談,于是,考慮到現代社會原則上就無法保證充分就業這個經濟學事實,邏輯上自然的后果就是總有一部分人被命運蠻橫地宣判為沒有價值的人。
剛畢業的年輕人不太容易這么想,因為朝氣蓬勃,初入職場,覺得一切都還閃著希望的金色之光。但那是玫瑰色的假象,那不是人的經濟價值在閃光,那是年輕的經濟價值在閃光。過了35歲,年輕的價值急劇縮水,問題就來了。
如果把問題問得殘酷一點:我們究竟為什么覺得每個人都應該有價值呢?這個假設本身是不是在當代就是錯的?古代沒有這個問題,因為平均壽命就是三十來歲。近代沒有這個問題,因為工業化國家就沒有停止過殖民和戰爭,像絞肉機一樣消耗著社會上的過剩人群。二戰后,資本主義迎來了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和平擴張。在年輕人人數超過中年人的戰后初期,一切都還不是問題,中年人可以安居各種小型金字塔的頂端。等到社會年齡結構開始老化,沒有那么多金字塔尖分給中年人了,人類社會終于推車撞壁,無法再回避這個問題:人到中年,但受行業特性所限又無法提供超過青年人的經濟價值,甚至再過幾年可能也無法提供超過AI的經濟價值,你存在的意義是什么呢?
令人驚訝的不僅是這個問題沒有容易的答案,而且是它似乎壓根就沒有被社會充分討論和面對過。仿佛這里有一重禁忌,仿佛這個問題本身大逆不道。沒有心理和智識上的準備的結果,是許多人甚至是整個行業的人完全是用肉身的撞擊去探索它的答案。
并不是所有的懸崖都有完美的解決方案,但社會至少有義務提醒大家懸崖的存在,有義務把這個問題擺到臺面上來。要么打破假設,要么重構價值。要么就像現實一樣,眼睜睜看著前仆后繼的人在毫無準備的時候跌下去粉身碎骨。